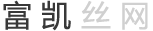美国陆军36师第131野战炮兵团2营(“失落营”)和美国海军休斯敦重巡洋舰上的官兵,被地狱航船送到樟宜战俘营,随即又被送到缅泰死亡铁路修建现场。美国学者凯利E.克拉格在《Hell Under The Rising Sun》(中文版《缅泰死亡铁路》,重庆出版社)对这些幸存官兵进行了访问,结合档案材料写出此书。战俘们对对樟宜战俘营留下了大量回忆。
日本人命令英国军官负起樟宜战俘营的管理责任,他们对战俘的饮食、医疗漠不关心,却强调战俘们一定要遵守他们制订的各种规矩。虽说是英国军官负责,但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和韩国看守经常巡逻。
铁丝网将樟宜战俘营与新加坡岛陆地相接的部分包围起来,没有铁丝网包围的那一面是茫茫大海。如果战俘想要逃跑,必须游过鲨鱼出没的海域。日本人根据国籍隔离战俘,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和其他几个国家的俘虏都被铁丝网间隔开来。樟宜战俘营的隔壁就是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樟宜监狱。
樟宜战俘营原本是英军修建的豪华军事基地,战俘们住宿倒不显得拥挤,数百名美国战俘住在一个大型的三层营房中,虽说不宽敞,但也不显得过度拥挤。日本人不给战俘们提供床,美国战俘于是四处收集材料来打造自己的铺位。火炮修理员赫伯特·莫里斯找来了英军废弃的医疗担架,修好了它,并做成了自己的床。其他美国战俘各显其能,有些胆大的从日本看守那偷盗木材做床。还有一些搜集废旧金属做成床架,上面铺上毛毯或者简易床垫。普拉格瑞特·克尔成功地用废旧管道早出了淋浴设施,俘虏们可以洗澡了。
战俘营里的各种蚊虫、臭虫快把战俘们逼疯了。各种昆虫在他们入睡,就开始折磨他们,尤其是臭虫,开始吸他们的血。赫伯特·莫里斯回忆了他与臭虫的斗争:“当你把床上的一起丢到一边,你就能够正常的看到该死的臭虫开始往墙上爬……数量很大,好似你在墙上乱泼了棕色的油漆,斑斑点点的。你在床上翻身,身子底下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很多臭虫被你压死在身下。你掀开床垫,床板上的血迹就好像有人被杀死在床上。床垫上到处是它们从你身上吸的血。你有冲动,想要捣碎它们。我快被逼疯了。”
莫里斯和其他战俘找出了对付臭虫的不同的方法,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他们在四个床腿周围放上水或者油,臭虫们无法爬过这些液体,对他们的骚扰程度减轻很多。夸脱·戈登熬过了一个被臭虫嗜咬的晚上,大清早他就起床,把床拖出营房,他抖抖床垫,打开床板,掉下来的臭虫“就像胡椒面洒在了地上。”
由于饥饿和缺乏药品,战俘们开始患病。主要是缺乏维生素导致的脚气病和糙皮病,以及痢疾。生病的战俘被送往战俘营的英军医院,不过那里缺乏药品,只能进行基本的治疗。药品和医疗用品,主要是战俘们被俘之前各自军队配给的,他们带到了樟宜战俘营,获得药品的另外一个途径是通过地下黑市,不过药品十分昂贵。
食物实在是非常匮乏,大米是他们的主食,一天三顿。早上是大米粥,里面时常出现鼻涕虫和蠕虫。日本人基本上只供应大米,没有调味料,所有战俘们到处寻找可供调味的东西,他们我们自己所带来的野战口粮当中的蔬菜和肉类,这样一个时间段起了大作用。但是这么多东西只是他们刚开始步入樟宜战俘营的时候有得吃。艾迪·冯记得日军给他们配给一份羊肉,不过冷冻的羊肉上写的年份却是1931年的。虽然羊肉不足以让每个战俘吃到一块,但是战俘当中的厨师们还是让战俘们的饭菜充满了“炖肉”的味道。他们用以调味的最主要的调味品是通过地下黑市获得的新加坡出产的红辣椒和花生,战俘们喜欢用它们拌饭。
随着在樟宜战俘营关押的日子变得久长,美国战俘的补给品消耗殆尽,他们开始用身上携带的少量的美元与澳大利亚、英国战俘交易,以获取宝贵的粮食和调味品。休斯顿号上的水兵保尔·帕普为了补充自己身体的维生素,翻捡自己的粪便,找出西红柿种子,希望种出西红柿来。他说:“我的那种饥饿用语言无法形容,老天,我需要食物,可是没有人给我食物。”
除了参加缅泰死亡铁路的修筑外,史拉兰广场事件是樟宜战俘营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了,也是战俘与日本当局关系的分水岭,日军之前表面上让战俘自治的面纱被彻底撕下来。史拉兰广场事件是战俘与日军当局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这个对抗性事件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1942年3月7日,日军开始逼迫战俘修建铁丝网,但是这个铁丝网并没有对战俘造成实际上的行动的限制。3月21日,日军突然发布命令,决定处死三名试图越狱的战俘,日军最高司令部下令,不准战俘逾越铁丝网,对于逾越铁丝网的行为要执行连坐政策,战俘要到铁丝网外面必须得到战俘中师级以上军官的许可,并携带日军发放的通行旗帜。当天,日本人在印度俘虏中策反的叛徒组成了印度伪军,开始在铁丝网边站岗放哨,日本人规定,无论战俘什么级别,都必须向印度伪军敬礼,遭到战俘一致,战俘们拒绝向叛徒敬礼。
随即日军取消了军官佩戴军衔的权利,并开始用日语下达口令,并要求战俘作出相应回应,日军不断强化统治地位,战后被缴获的一份日军管理当局的文件显示,日军“要向对待广东苦力那样对待战俘”。
日军不断将战俘营的骨干力量编成劳动队,派到新加坡以及另外的地方劳动,日军认为战俘营的凝聚力和斗争能力大幅度削弱。劳动力大量被抽调,战俘们不得不加大劳动时间,以维持粮食和蔬菜的生产,军官们发布指示:“捕鱼和耕作成为战俘营头等大事。”
8月31日,一名印度司机给英军弗兰西斯・马吉少校传递了一张纸条,纸条显示,日军准备处死英军俘虏布里文顿下士、盖尔列兵、沃特斯列兵和弗莱彻列兵。马吉少校随即委派巴斯尔・卡德伯里・琼斯上尉赶往日军驻樟宜司令部,向日军当局递交请愿书,日军高级军官当场把请愿书撕碎扔到了琼斯上尉的脸上,随即又将碎片捡起来,塞进琼斯上尉的腰带。英军抗议无效,4名战俘随即在樟宜海滩被印度伪军枪毙。日军强迫战俘观看行刑过程。
9月2日,日军将战俘集中到史拉兰广场,强迫战俘签署不再逃亡的宣誓书,战俘们予以拒绝,认为是极大的侮辱。于是日本看守当局派遣了荷枪实弹的印度伪军,将广场团团围住,只要有人越过日军设置的警戒线,就会被印度伪杀。日军则在广场四周架起机关枪,并切断了主要水源。广场上没有一点遮阳的东西,战俘全天在在烈日下暴晒,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铁丝网中,广场地方狭小,他们没办法躺卧,只能站着或者蹲着。
为了逼迫战俘签署宣誓书,歹毒的日军看守当局,将战俘医院里的病号也赶到了广场上,病人中有很多是痢疾、白喉等高传染性疾病的患者,日军为了向战俘施加压力,丝毫不把战俘的生命当回事,这道命令不仅会将病患置于死地,也会让很多战俘感染上这些致命的疾病。
高级军官们与日军展开了紧张的交涉,最终日军同意了他们提出的宣誓书的修订方案,高级军官们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疫情的全方面爆发,决定让战俘签字。史拉兰广场事件告一段落。
1942年9月至1943年9月,樟宜战俘营的战俘被日军强征充当奴隶劳工者慢慢的变多,樟宜战俘营战俘人数从1942年的21154人,下降到1943年的5307人。在此期间,由于日军从外地抽调的战俘劳工经过樟宜周转到缅泰死亡铁路的现场,樟宜战俘营人数一度回升到28207人,随着这些战俘被送到缅泰死亡铁路现场,樟宜战俘营人数又再次回落。
1943年秋天,参与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战俘回到樟宜战俘营,随即所有战俘又在1944年5月,被移到樟宜监狱。他们在樟宜监狱迎来了解放。在樟宜战俘营存在期间,日军不断征调战俘到缅甸、泰国、台湾、日本等地充当奴隶劳工。日军在1944年5月要求战俘前往樟宜监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中了樟宜基地良好的居住条件,日军自己要住,所以战俘们被迫搬家了。
在樟宜战俘营的盟军战俘中,英军的死亡率是26%,美军是33%,澳大利亚战俘是36%。据美国学者加万・道斯统计,在太平洋战争中约有27%的战俘丧命于日本人之手。细分到国别,美国战俘的死亡率大致为34%,澳大利亚战俘为33%,英国战俘为32%,荷兰战俘为20%。樟宜战俘营中关押过的战俘为如此高的死亡率贡献了很大的比例。在日军从樟宜战俘营抽调的奔赴缅泰死亡铁路工地的“F”工作队中,英军死亡人数是60%,澳大利亚是29%。澳大利亚在二战期间有25000名军人死亡,其中8000名死在战俘营,在这一个数字中,樟宜战俘营中的澳大利亚战俘占相当大的比例。落入日军手中的澳大利亚战俘,差不多有一半死在日本战俘营中。
以上数据统计的都是以在樟宜战俘营关押过的战俘为标准统计的,并不是说所有战俘都在樟宜战俘营丧生,事实上,我在前文说过,樟宜战俘营就是一个中转站,参加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英、美、澳、荷等国战俘,都在这里关押过,而且缅泰死亡铁路只是他们工作的一个地点,事实上,他们很多人被送到了日本本土、台湾、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等地充当奴隶劳工,很多人死在了工作的地方,或者在去的路上丧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