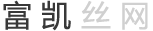1952年,一位老革命家曾说:"当年若不是这场隐秘商洽,赤军或许就要支付更大的献身。"这位老革命家便是何长工,而他口中的隐秘商洽,竟牵扯出了一位让蒋介石都意想不到的重要人物。
1934年10月的一天,中心苏区下起了绵绵秋雨。在瑞金叶坪的一间粗陋会议室里,赤军总部的灯火今夜未熄。这是赤军第五次反围歼失利后的第三天,局势现已到了危如累卵的境地。
但是,这个期望却几乎被内部不合所打破。军事三人团成员之间对是否该与陈济棠商洽产生了剧烈争辩。一些人以为这或许是敌人的骗局,另一些人则忧虑商洽会露出赤军的战略目的。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危殆时间,一个斗胆的主意在赤军高层中逐步构成:或许能够寻求与陈济棠达到某种默契,借道包围。这个主意尽管冒险,却是其时最实际的挑选。这也为后来的隐秘商洽埋下了伏笔。
何长工和潘汉年的这次使命之所以能够成行,还要从周恩来的一场剧烈争辩说起。其时的军事三人团中,博古和李德都对立与陈济棠进行任何方式的商洽。他们坚持以为,这样的商洽会露出赤军的战略目的。
在一个叫做"三岔口"的小村庄里,他们遇到了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这位联络员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音讯:陈济棠现已派出了自己的亲信,正在隐秘等候赤军的代表。
这场森林深处的隐秘会晤继续了整整三个小时。两边商洽的内容都记在一个特制的小簿本上,这个簿本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史料。不过,其时的参与者们或许都没想到,他们正在书写前史的重要一页。
1934年10月18日的深夜,商洽刚开端不久,又一个意外发生了。一位联络员仓促赶来陈述:蒋介石派出的密电被地下党截获,电文中正告陈济棠不得与赤军有任何触摸。这一条音讯让两边的商洽气氛一度变得非常严重。
两边为此争辩了整整一天一夜。最终,何长工抓住时机,决议暂时放置这些政治条件。他提出:燃眉之急是处理借道问题,其他工作能够今后再谈。这个主张得到了潘汉年的支撑。
但是,商洽的内容有必要肯定保密。两边约好:一切的协议内容都只记在笔记本上,不留任何正式文件。这些笔记本后来都被销毁了,成为了前史的隐秘。
第一项协议最为要害:粤军许诺在赤军经过期后撤二十里,但要求赤军有必要提早24小时通报详细道路。这个协议看似简略,却为赤军的包围拓荒了一条生命通道。
第五项协议则是最特其他:假如发生意外状况,两边约好了一套应急预案。比方,若遇到中心军的忽然查看,粤军能够标志性地开几枪,以作保护。
随后几天,陈济棠开端悄然地调整部队布置。他把最信得过的部队组织在要害方位,一起将那些或许不太牢靠的部队调往其他当地。这些调集看似是正常的军事布置,实际上却是在为立刻就要降临的举动做准备。
1934年10月25日清晨,一支赤军先遣队悄然无声地出现在第一道封锁线前。依照事前的约好,粤军现已悄然后撤了二十里。就在蒋介石还在南京等候战报的时分,赤军主力现已悄然经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这一切都让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依照他的布置,三道封锁线应该是风雨不透的。但是赤军却像一缕轻烟相同,从这些紧密的防地中轻易地穿了曩昔。
过后,陈济棠在向蒋介石的陈述中写道:"赤军举动诡秘,我军虽奋力追击,仍让其突出重围。"这份遣词慎重的陈述,成了这段隐秘前史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