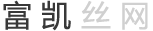10年前,这里还过着原始闭塞的农耕生活,10年后,这里种上经济作物摆脱了贫困
一个百年未变的高岭苗乡,怎么样才可以改变贫穷与闭塞的生活,真正进入现代化的生活之中?
永胜村,位于云南屏边县大山深处的一个苗族村寨,2000多人散落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中。10年前,这里还过着原始而闭塞的农耕生活,进出无路,沟里无水,人们在陡峭的坡地上刀耕火种,年收入不超过2000元。10年之间,这里通过外出务工和种植经济作物,踏上了摆脱贫困之路。
有人踏出群山,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也有人回归故乡,振兴家园。对他们来说,脱贫不仅仅甩掉了穷帽子,更是一次人生的改变,一次追逐现代化的负重爬坡之旅。
2020年7月5日,云南红河州屏边县永胜村。天边刚刚露出微曦,小学校的起床音乐在山间响起,住校的孩子们一个个起床。
小学校外面的一个院子里,54岁的永胜村党总支书记杨国林细心地把一捆捆芭蕉叶切碎,再拌上玉米面,去喂自家的4头牛。
杨国林家是一栋2层的砖房,屋顶吊脚,保留着苗族建筑的风格,墙面和柱子上的红砖在外,有些已经磨损了。就在他家的旁边,几栋崭新的小楼依次矗立,青瓦黄墙,巨大的落地窗上有传统的木格,水泥钢筋的房屋上,又搭建起苗式的吊脚楼。
“7年前,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现在,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忙过一阵儿之后,杨国林坐在院子里,捧起水烟筒,一边休息,一边对记者说。他的妻子则在厨房里做早饭,白米饭,地里摘的新鲜蔬菜、一小块腊肉、山上找来的菌子,组成了他们一家四口的早餐。

永胜村是一个纯苗寨,全村下辖7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99.7%的村民是苗族,村委会所在的自然村叫做“母租白”,100%都是苗族。

母租白是一个“彝语”译名,意为“太阳最晚落山”的地方。百年前,这里还是彝族聚居地,后来彝族村民遭难迁徙,杨国林他们的祖先便在这里落脚,但原来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
过去数十年中,这个大山中的苗寨似乎一直遗落在时代的洪流之外,村民们延续着传统的农耕生活,在陡峭的山坡上种玉米,在河沟里种稻子。山地贫瘠,庄稼的产量不足外面的一半,玉米丰产时,亩产不过300-400斤,年景不好,可能颗粒无收。数十年前,村里每年有三成的村民,要靠政府发放的救济粮度日。
杨国林就出生在母租白,他和记者说,那时候,一家人住在土房中,一年到头,粮食都很紧张,养一头猪,过年杀了,卖几个钱,就觉得是最“美好”的生活了。
村里的环境更差,茅草屋、土坯房随意乱建,村里的道路都是土路,再加上禽畜乱跑,到处都是粪便,一下雨,粪便和泥泞混合在一起,要穿长筒雨鞋才能出门。母租白——“太阳最晚落山”这个颇有诗意的名字,没人会提起,人们更多用“猪屎村”来称呼这个村子。

2007年,杨国林走出大山,到州府蒙自的一家葡萄园打工,他是第一个走出母租白的村民,也是整个永胜村7个自然村里最早外出务工的。
2010年,响应屏边县政府号召,发展本地农业产业,杨国林从葡萄园辞职,回到村里,准备种植枇杷。“刚回来的时候,觉得不能适应了,不是村里变好了,而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后,忽的发现,自己的村子怎么会这么差?”
王广平也是最早外出务工的那一批,他出生于永胜村的另一个自然村格咪底,结婚后分家独立,他借遍了亲戚,盖起一栋砖房。房子盖起来之后,他就和妻子外出打工,赴新疆种棉花。
“那时候,外出打工的人特别少。”王广平说。世代居住在大山里的村民,既不熟悉外界,也对外界的生活不感兴趣。再加上大多数人文化水平很低,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算账,给人干一年,连自己赚多少钱都算不清楚,也就不想出去了。
2014年,全国贫困户建档立卡,永胜村有贫困户257户1136人,占全村1986人的一半还多。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不愿意外出务工,永胜村所在的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和记者说,他到每一个村里,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村民开会,开会的唯一目的,就是告诉高山苗寨里的村民们,外面的生活是怎样的,山里的村民们,又该过怎样的生活。

“一直处在闭塞环境中的人们,不知道外面的生活是怎样的,自己吃穿住行都成问题,但还觉得挺幸福。所以一定要帮他们改变观念,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这才能让他们有改变自身生活的动力,才能不满足于这种最原始的‘幸福感’。”杨富丞说。
杨国林也有同样的感受,村民们不愿意出门,脱贫攻坚刚开始的时候,政府曾邀请企业到永胜村招工,结果被村民当成骗子,赶了出去。
不过,反复的思想工作,以及先行者的示范效应,终究起到了作用。“我是母租白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也是第一个盖砖房的,2013年,我的房子盖起来,是当时村里最好的。一下子,很多人相信了,外面能赚到钱。”杨国林说。
王广平和同去新疆打工种棉花的村民们,也在过年时带着钱回家了,这也成为了村民参考的对象,“那几年,永胜村外出打工的人多了起来。”杨国林说。
从杨国林盖房子到现在,7年过去了,杨国林的砖房已经有些旧了,但村里更多的新房子盖了起来。和杨国林老式的砖房不同,新房子大多是明亮、鲜艳的新式小楼,就在杨国林的左右隔壁,他的两个兄弟的小楼都是新盖的,巨大的落地窗,把阳光引到室内,屋里窗明几净,所有现代化的家具一应俱全。相比起来,杨国林昏暗的家里,显得有些陈旧了。

近几年来,永胜村有两波盖房子的高峰,第一次是2014年,村主任熊国清和记者说,2014年,云南省红河州启动 “美丽家园”计划,鼓励村民改造旧居,最高的政府可以补助3万元。但实际上,3万元不足以盖起房子,更不可能盖起小楼。“其实政府救助主要是撬动作用,那时候,村民们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也开始有钱了,但刚刚有钱,很多人都攒着,没想过要改造、重建原来的危房、土房。政府补助恰好让他们有了一个契机,自己掏出打工赚来的钱,加上政府补助,就把房子盖起来了。”熊国清说。
永胜村最初的务工者,大多在新疆种棉花,这是一份收入有保障且不要多少专业技能的工作,所以颇受欢迎。种棉花赚了钱,回家盖起来房子,这些房子就被村民们叫做“棉花房”。“村里一多半的房子,都是棉花房”,熊国清说。
7月7日下午,杨国林到77岁的王英兰家,告诉她,过两天有乡镇的演出团到村里演出,如果想看,可带着孙子一起到村委会院子里看。
这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也是一个有特殊困难的家庭。王英兰家原本有7口人,她,儿子儿媳,4个孙子。王英兰的儿子早年外出务工,2018年,儿子在工作的地方意外昏倒,随即去世。王英兰已经年老,4个孙子还小,只有儿媳妇杨美芬一个劳动力。

儿子的去世,不仅意味着家里唯一赚钱的劳动力没了,更重要的是,家里所有人都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走的是活着的儿子,回来的只有一个盒子。”坐在小板凳上,王英兰反复重复着同一句话,“不认得”。
旁边的杨国林向记者解释,王英兰的意思是,回来的骨灰盒,她不认得那是她儿子。
2018年,全国农村危险房屋改造政策推行,王英兰家的房子符合危房标准,政府补贴3万元,为她家盖了一栋新房子,挂包永胜村的屏边县政协干部,则出资为他们购买了家具,同时动员儿媳妇杨美芬外出务工。

儿子出去打工了,老人背着刚出生不久的孙子下地干活。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最开始,王英兰不同意儿媳妇外出打工,杨美芬自己也不愿意。”杨国林说,村干部们反复做了很多次工作,才说动这一家人。“其实能够理解,家里就一个劳动力,剩下的老人小孩,杨美芬自己也不放心,但我们告诉他们,家里的事情有人管,两个大一点儿的孩子都住校,老人主要管两个小的吃饭问题,其他都有人帮忙解决,这才说动他们。”
如今,王英兰已经改变了想法,不再提之前反对儿媳打工的观点,“不出去找钱,怎么生活呢”。问起家里的收入,她也只是说“不认得”,她不识数,不知道收入多少,但知道儿媳会定期寄钱来。
王广平也在打工中失去了孩子,2014年,他们夫妻带着刚出生不久的老二去新疆打工,1年之后回到村里,孩子就得了麻疹。那年过年,他们把县里、州里的医院跑了一遍,赚的钱全都搭进去了,但孩子还是没留住。
孩子没了,生活还得继续。只是第二年,他们不再去新疆了,转到江苏,进了一家纺织厂做工。
更多的打工者,把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甚至把盖了一半的楼也留在了村里,重新出去“找钱”,等赚到了钱,接着盖。

干沟自然村的李美英家,就在村里主干道的下面。74岁的李美英刚刚吃过了午饭,走出家门口,打算去村里走走。她身后的二层小楼,只有第一层是盖好的,门窗家具俱全,李美英就住在里面。第二层则只有一个框架,窗户、屋顶都没有盖好。
“盖到一半没钱了,孩子们出去打工找钱去了,找了钱接着盖”,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李美英也把赚钱说成“找钱”。
李美英有4个儿子,她住的房子是老四的,老三的房子和老四挨着,也是新的,但只有一层,“老三还没结婚,所以一层也够了,等结婚了再说”。
在永胜村7个自然村里,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村里甚至到处都能看到盖到一半的房子,“一般第一层都是政策补助盖起来的,后来村民们赚到了钱,自己加盖。有的盖到一半没钱了,就出去打工赚钱,赚到钱再回来接着盖。”村主任熊国清介绍。

村委会的会议室里,已经坐了7个人,包括村主任熊国清,村监委会主任李富林,驻村宋国伟,以及4位来自县乡各单位的驻村工作队队员。

村委会会议室里,村干部和年轻的驻村工作队,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驻村工作队是屏边县在脱贫攻坚中帮扶贫困村的人才措施之一,全县每一个行政村都有一个工作队,一般贫困村3个人,像永胜村这样的深度贫困村则是5个人。他们负责所驻村的贫困情况调查、政策解释、政策宣传、政策落实等一系列具体的工作。
上午的时候,5位工作队员在镇里听了一次例行的扶贫工作讲座。下午2点的会,宋国伟简单地传达了上午的讲座内容,并分派工作队下午的工作。
10分钟左右的会,总共两个人发言,从县纪委监委参加驻村工作的宋国伟,发言简短但正式,村党总支书记杨国林则显得干脆,还有一些农民的直率和随意。
会开完,几个人分了三组,下午的工作是检查各村各户的人居环境,并给每一户评分。分数进行累计之后,每个月都可以到村里的爱心超市兑换各种生活用品。
来自屏边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队员任建瑶和村主任熊国清一组,去干沟村检查。干沟村在母租白的东南方,骑摩托车差不多要走20分钟左右,然后对每家每户进行全方位检查、评分。
任建瑶的手里,有一张干沟村的卫星地图,地图上手工标注了每一栋房子的户主名字。

任建瑶和记者说,这样的地图,每个自然村都有一张,都是工作队员们在一家一户的调查中一点点记录的。

同样来自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队员张春梅,正打算把这些图制作成电子版,一方面能够提供给其他村干部使用,另一方面还可以在人口普查时作为参照。
外出务工给闭塞而贫穷的苗寨村民们,带来了新的生活。然而,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本身也造成了许多的新问题。

驻村工作队帮助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更多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如王英兰,尽管有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县乡挂包单位干部的帮助,但儿媳妇外出打工,抚养孙子们的工作,大部分仍要靠她完成。这对一位77岁且多病的老人来说,负担仍然极重。
“乡村的振兴,得有乡村自身的动力,外出务工确实可以帮助贫困家庭快速脱贫,但也会带来劳力流失、妇孺留守等问题。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才能让村子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新现镇党委副书记黄涛说。

然而,屏边县山高沟深,生存环境恶劣,长期以来,也只有少数规模的产业,如何在大山里发展起自己的产业?事实上,过去许多年里,包括在扶贫脱贫的工作中,屏边县也曾尝试过很多产业,但多数不算成功。于是,在2010年左右,屏边县开始从自身的传统产业——农业出发,寻找发展的契机。
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和记者说,2014年以来,屏边县重点推动枇杷、荔枝、猕猴桃等几种特色水果种植,新现镇地处高海拔区域,适合枇杷种植,而永胜村是枇杷产业发展较快的村子。
杨国林还很清楚地记得,当初推行枇杷种植的困难。村民们不愿意,矛盾一度难以解开,甚至在村民大会上发生了争执,“当时政府出资买苗,政府帮忙种植,一直到3年挂果,再还给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也就是说,村民什么也不用管,等3年收获就可以了,即便如此,一开始也没什么人愿意种”。
王广平就是不愿意种的村民之一,他们一家常年在外打工,并不看好枇杷种植的效益,也没时间打理。更多人担心枇杷种植会影响种玉米。种玉米收获不多,但当年就有,种枇杷3年没收益,3年后怎样还不知道,所以大部分村民不同意。
杨国林说,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王广平,他是村民小组的组长,动员他起带头作用,而且也不用自己投入,3年后看成效。再比如担心不能种玉米的农户,就会告诉他,枇杷树刚栽的时候要遮阴,可完全套种玉米,不影响,无非就是少种几棵玉米的事情,等到结果了,也就有收益了,就不用套种了。
王广平最终种了12亩枇杷,2019年第一次挂果,到2020年,12亩枇杷卖了8万多元。村里种的最多的,可以卖到10多万,少的也有四五万。永胜村的枇杷产业正在逐渐成型,更多的人开始主动扩大种植。“现在有200多户种植枇杷的。”杨国林说。

王广平如今已经不外出打工了,而是留在家里种植枇杷。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村里的产业在发展,但村民们的素质仍待提升,杨国林和记者说,挂果之后,政府把枇杷地交还给村民管理,但很多人缺乏技术,也缺乏管理的意识,“怎么剪枝,怎么疏果,都要学,但一开始,学的人少,有的人干脆就扔在那里不管,长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因为以前的玉米也是这么种的,撒了种子,就不用怎么管了”。
从完全靠天吃饭的玉米种植,到需要精细管理的果树种植,村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挂包永胜村的县政协年年都会邀请农业技术人员,到永胜村的各个枇杷地里进行现场教学,教村民们如何在果树生长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更好的管理。
7月9日,新一次的培训在格咪底村的枇杷地里进行,培训的老师是县林业局的技术员,永胜村各个自然村几十村民走到地里,跟老师学习怎样剪枝塑形。

“树的中心要剪开,透光透气,在合适的地方让侧枝生长,还要给侧枝塑形,让它们分布得更合理……”
培训老师就着地里的枇杷树,告诉村民们如何管理,顺便纠正以前管理的错误之处,有人钻到树底下听,有人不断地提出问题,跟着父母一起来的孩子们,则在山坡上撒欢儿。
一个多小时的讲解结束,老师被一位村民拉到自家地里请教,还有人站在路边等待,老师的时间只有半天,但工作还很多。
听课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王树元是其中一位,他骑着摩托车,带着4岁的小女儿一起,老师被拉到别人地里了,他坐在摩托车上等。

王树元带着4岁的女儿一起听课,他的枇杷今年卖了5万多,不打算出去打工了。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王树元和记者说,她和妻子原本也都在外地打工,但今年枇杷卖得不错,卖了5万多,妻子仍旧出去打工了,他就留在家里,一方面管理枇杷地,一方面也照顾孩子。
在永胜村,像王树元这样留下的,还有不少。杨国林和记者说,永胜村目前一共有5000多亩枇杷,其中2000多亩挂果了,这些挂果的枇杷,都需要有人精心管理,不能再放养了,更重要的是,枇杷的收益,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看到了在家里赚钱的可能,“能在家门口赚钱,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王广平夫妻俩也都留在了家里,打工七八年,虽然收入不错,但孩子们受罪太多,枇杷收益不错,他们都觉得,还是留在家里更好一点儿。
“种水果和种玉米不一样,随时随地都有活儿。”在王广平的枇杷地里,他指着一簇新发的枝条说,“这种新条,要随时剪掉,让营养保留下来,果子才能长得更好。而且枇杷成熟的时间非常长,从11月份到第二年2、3月,一直都在成熟,卖的时间也很长,离不开人”。

2019年底到2020年初的这一茬枇杷,价格不错,最高的可以卖到20多元每公斤,王树元和记者说,枇杷成熟的时候,山上的砂石路上,停了一溜大车,都是来收枇杷的。
“现在就是路还不好走,收枇杷的车进出挺麻烦,而且山坡上的田间路也不多,成熟的枇杷大部分还要靠人背马驮才能运到路边。”王树元说。
王广平的枇杷地边上,已经新修了一条环山的田间路,这让他的劳动量减少了很多,但仍旧不能够达到地头,“现在政府在不断地修路,未来会更方便吧”。
杨国林没有去听田间课,他和家人一起去了自家的猕猴桃地里锄草。他种枇杷不多,但种了30多亩猕猴桃,地就在格咪底村另一边的山坡上。
种果树10年,杨国林自己也成了专家,经常有外村的人来请他去指导。不过,他也面临着和王广平他们一样的困难——生产道路不足。“大部分耕地都是坡地,有些地坡度很陡,以前全靠人力和畜力,过去常有骡马从山坡上滚下来摔死,所以路很重要。”杨国林说。
7月9日一早,吃完早饭,喂完牛,杨国林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先去地里了,杨国林去了一趟村委会,然后才一个人走去地里。

走在村委会门前,杨国林没有想过,十年中他的村庄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从村委会到杨国林的猕猴桃地里,要走20分钟左右的砂石路,然后还要经过一条600多米的下坡土路,这条土路原本并不存在。2017年初,杨国林承包了山坡上的30多亩地,准备种猕猴桃时,才自己出资请人修的这条路,花了3万。这条路修成后,不仅杨国林家可以用,沿途的15家200多亩地也都方便种植了。
杨国林和记者说,包括树苗、供猕猴桃攀援的铁丝网、修路等,他一次性投入了30万元,“材料成本不算高,人工太高了,在平地上,干一天活100块,在山地上就得翻一番。”
2019年,杨国林的猕猴桃已经有了收益,卖了15万左右,2020年可能会差一点儿,“主要是天时问题,先是霜冻,后来又有冰雹,坐果不多,估计能卖五六万。”他说。
其实,杨国林想过要做设施农业,但在陡坡上盖温室大棚,成本过高了,而且道路没通,即便想投入,也还缺乏条件。
“当前,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仍存在不足,尤其是自然村之间的道路、田间道路,我们的规划中,也在不断地加强这方面的建设。”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说。
实际上,相比10年前,村里的道路已经完全改观,杨国林和记者说,这些年,各自然村里的路面硬化、自然村之间的砂石路铺设几乎都已完成,田间道路也增加了不少。
“最直观的结果,就是村里的车多了,没有修路之前,全村的摩托车一共也就5辆左右。2014年到2016年,是摩托车增加最快的时候,几乎家家都有摩托车。2018年到2019年,则是小汽车增加最快的时候,现在全村差不多有20辆小汽车。现在汽车还到不了地头,但摩托车可完全了”。
永胜村最远的一个自然村,叫岩羊冲,这个村一共12户人家,因为地处山体滑坡区域,已经全村搬迁到镇上。

48岁的杨保生,就是搬迁户之一。杨保生以前在州府蒙自打工,收入可供一家人生活,但搬进新家后,杨保生的妻子因病去世了,家里留下父女三人,两个女儿平时住校,周末回家。杨保生要照顾两个孩子,不能外出打工了,就在镇上打点儿零工,兼顾着原来村里的地。安置点有就业帮扶的人员,他们能够帮助像杨保生这样的搬迁户,就近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7月7日中午,记者在新现镇安置点的一栋居民楼中,见到了杨保生。杨保生的新家,是一个三居室,两个卧室住人,一个卧室当储物间,客厅向阳,很宽敞。记者发现,屋里的各个窗户都有崭新的窗帘,唯有客厅的落地窗没有窗帘,杨保生和记者说,是他故意没装的,“这样亮堂,畅快”。


骑摩托半个多小时,杨保生回到老房子边上的地里,地里还种着生姜。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从乡间公路转到山路,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杨保生就到了岩羊冲的老房子,老房子大部分都拆了,留了一小间当做工具间,也可以休息。房子是以前的土坯房,窗户很小,屋里一片昏暗,即便是中午,也要开灯才能看得见。
新现镇的安置点,楼房也是苗族风格,吊脚楼、米黄墙、木格窗。永胜村没有搬迁的其他6个自然村,新盖的房子也都多少保留着苗寨的风格。

相对于城镇里的居民区,村里的自然环境更好。硬化的水泥路边上,扎着竹篱笆,路边的花坛里,民居的房前屋后,长着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高大的椿树;小叶的樟树;结着红色果实的构树;攀援的百香果垂下长长的枝条,上面绿色的百香果刚刚泛白,还没有完全成熟;蓝花草的花正在盛开,蓝紫色的花朵迎风摇曳;本地的香脆李慢慢的开始转黄了,再有10来天就可以吃了;还有随处可见的两面针;以及和两面针长得很像的刺天茄;偶尔才能看到一株的名贵中药材重楼……
“我们这里村庄绿化,除了少部分是外来物种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本地常见的草木,还有很多经济作物,比如香脆李、枇杷等,政府鼓励村民在房前屋后栽树,还有一定的补助,一方面绿化村庄,一方面也能给村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说。

正在盖房子的杨祖德的院子里,养了100多棵重楼,种在10多个大大小小的花盆里,大的有10多棵,小的三五棵,这些重楼他养了2年多了,去年他带到集市上卖了一小盆,700块钱。剩下的,他想再养养,“重楼用的是根茎,长得越大越值钱”。
7月10日傍晚,山里下起了细雨。位于母租白的永胜村委会院子里,几个工作人员正在雨中安装音响、布置舞台,一块巨大的幕布挂起来,但因为风大,又撤了下来。
这是新现镇文艺演出队“送戏下乡”的活动,演出的演员都是来自各村文艺队的群众,永胜村也有10多个人参加。
因为下雨,演出拖延了一段时间,等待的过程中,杨国林又看了一下村里人均收入的数据,10年前,母租白村人均年收入1600多元,10年后的今天,已达到了6000元,超出了脱贫的标准。
王英兰穿着一身红色的苗族服装,坐在最前面一排,两个小孙子就在旁边,看演出的时候,她的脸上没那么严肃了,笑容多了一点儿,杨国林过来和她打招呼,她笑着回应了一句。

王广平坐在人群里,不仔细找,很难发现他。几年前,他在这个院子里曾经反对过,犹豫过,也矛盾过,最终同意种了枇杷。如今,他感觉自己选对了。
晚上7点多,演出真正开始了,这一段时间,正好是母租白日落的时候,只是阴天看不见太阳在群山间落尽的景色。
灯光亮起,好戏开锣。演员们轮番登场,有讲述脱贫故事的,有关于疫情防控的,也有描绘苗乡风情的,永胜村的文艺队演了三个节目,有苗族舞蹈,也有苗族芦笙表演。

最后上场的是杨国林,他不会跳舞,但在场上手舞足蹈,大段的方言夹杂着苗语,似乎在感叹永胜村巨大的变化。他也不怎么会唱歌,但突然唱几句,村民们则会报以一阵笑声。